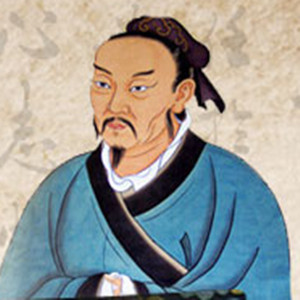杨海文先生(左)梁涛教授(中)孟小红院长(右)
传统文化的普及与提高
宋立林(后面简称宋):杨先生您好,感谢您接受采访!您的作品我读过不少,特别佩服您把非常深的儒家之道,写得那么生动。对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,真能做到这一点,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。请问您是否有意或者说是自觉地这么做的?
杨海文(后面简称杨):没有刻意!
宋:我们在传统文化普及或弘扬的过程中恰恰需要这样一种方式。学者们如何面向更多的人,更大众化一些,不知道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想法?
杨:普及与提高这个问题,我经常思考。佛教有两种类型,一是大乘佛教,一是小乘佛教。小乘佛教关注于自身解脱,大乘佛教普度众生。受这两个观念的影响,我这么多年来的写作,既想提高自己,也想普及。
我特别感谢我上武汉大学的那个特定时代,就是80年代。当时有部电视政论片叫《河殇》,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论文就是写它的,发表于《湖北社会科学》(1988年第12期)。《河殇》是反传统的,但在反传统的大潮下面,也有一些做学问的。鉴于我的学力,只注意到很有名的,比如李泽厚。李泽厚影响到整个80年代。大三我写了《李泽厚的心灵世界》一文,大四发表在《随笔》(1989年第2期)。以上两篇文章是我本科时期写得较好的东西。写《河殇》的,立足于提高、深层分析;写李泽厚的,比较感性,属于普及类。这个“两条腿走路”的做法,影响我很深。
后来研究孟子,很偶然。业师李宗桂教授主编《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》,让我写孟子,我起先答应了,后来还是没写,原因是我对孟子还不怎么了解。但是写硕士论文,还是确定了写孟子,题目是《孟子与〈诗〉〈书〉文化》,主体部分发表在《孔子研究》(1997年第1期)。后来读博士,也研究孟子。一个人研究哪个领域,其实很多时候出自偶然。偶然也是机缘,也是缘分。
我在哲学系上硕士、博士,基本上按照哲学的思路写孟子。哲学解释是我第一个阶段的东西。立林看到我的一些作品,是用文学的方式说孟子,算第二个阶段。现在,我是按史学的方式做孟子,属于第三个阶段。
这些年,我主要研究孟学史,零零散散做过一些案例。比如汉文帝时期的《孟子》传记博士,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怎么样,值得思考。朱元璋时期的《孟子节文》问题也很重要。过去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不多,即使关注也是随感似的。改革开放后,研究者大多立足于义理层面,讲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怎么引起了朱元璋的反感。这些都不难解读,但《孟子节文》这件事的来历怎么样?《孟子节文》事件之后,哪些人做过回应?研究这方面的很少。我的思路就是把更多的文献找出来,充分占有第一手的、原始的文献。
《孟子》这个文本之外,还有很多话被视为孟子讲的,称为《孟子》佚文。《孟子》有不少佚文,清代学者做了很多研究,但不同学者,抄出来的不一样。从今天的学术规范看,他们没有出具真正标准的文献来源,难以显示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,特别是文字上的差异。我们再做《孟子》佚文,就该更细致、更精准些。
对传统文化,有批的,也有维护的。我们不能限于口号,应该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。如果我们静下来做,每个人做一点,做一个部分,那么,所有的部分加在一块,可能就是比较丰硕的成果。我走上孟子研究这条路很偶然,但好比包办婚姻一样,一旦包办了,我就安安心心在这个婚姻里面了!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一样,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己选择职业,是职业选择我们。

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化守成主义
宋:您的书中提到两个方面,一个是道德理想主义,一个是文化守成主义。这一点我们深有同感。不过,对于道德理想主义和文化守成主义本身,学界和思想界有不同的看法,尤其是前者,更是受到很多责难。您对于道德理想主义如何看待?
杨:这个问题很大,我按实际感受谈谈看法吧。我的《浩然正气——孟子》以及即将出版的《文以载道——孟子文化精神研究》用了这两个概念,就是道德理想主义、文化守成主义。又有一个东西把它们整合起来,就是文以载道。文以载道就是通过文化守成主义来达成道德理想主义。为什么要说通过文化守成主义来达成道德理想主义呢?我们回到孟子,回到儒家,他们追求内圣外王,但外王的理想很难实现,古往今来,外王理想能实现的有几人?比如王安石、张居正,可以说是成功的政治家,但是否是真正的儒家,很难划界。
崔海鹰(后面简称崔):其实尧舜之后吧,真正能够把儒家内圣外王实现到外王这个境界的,只能说是得君行道而已。
杨:历史上,得君行道者也是少数。对于孟子,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,他们参与社会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呢?就是文以载道,就是通过文化理想、文化建构来实现或者把它们推广出去,变成整个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,所以文以载道就是通过文化守成主义以达成道德理想主义。
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包括几个方面:仁且智是一个方面;还有经权之辨;再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参不参与政治,所谓的士仕观。文化守成主义呢,我认为第一个是学孔子,孟子有一个理想就是学孔子,这是他的一个大理想;第二个就是距杨墨;第三个就是他对诗书文化,有一套解释方法。有人认为这个方法跟西方经典解释学可以相提并论,也有道理。我从六个点(仁且智、经而权、士则仕、学孔子、距杨墨、尚诗书)、两条线(道德理想主义、文化守成主义)、一个面(文以载道)把孟子文化精神开掘出来,这是哲学解释的方式。
作为古老经典的当代阅读者、解释者,我的内心里有许多信念,但这些信念到底是孟子的还是我的,相信大家在研究的过程中,很难分出来。原作者的意图跟解读者的意图,有时候就是分不清。如果不搞研究,不写论文,只是看孟子,你的思想不必以文字的形式显示出来。一旦拿起笔,开始写,那么,这个思想到底是杨海文的还是孟子的,是很难分清的。
尽管如此,我解释孟子,有我的立场。当代社会,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整个文化处于边疆地位,政治、经济绝对是舞台上的主角。我们在边缘的位置,该怎么办?有的知识分子可能离开文化这个疆域,进入到政治、经济的中心,这是一种。但是你已经被同化了,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。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留在文化这个领域里,去对当代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产生影响,方式就是文以载道,就是通过文化守成主义来达成道德理想主义。这种立场又跟激烈反传统不一样,可以称为文化保守主义,但我没有用这个词。因为,以前一些作品里,与文化保守主义相对应的词是政治自由主义,两者有对应关系。文化保守主义、政治自由主义的解释框架比较适合20世纪以来受西方学术思潮影响比较大的知识分子,比如梁漱溟、胡适、蔡元培等,但我们不能拿20世纪的解释模式套到孟子身上。我为什么选文化守成主义而不是文化保守主义,也是立足于这方面的考虑。
宋:孟子本身是守先待后。文化守成主义,我见过汤一介先生最先使用这一说法。当时感觉,这个词比文化保守主义要好,“那种”色彩更淡一些。在一般知识分子心目中,文化保守主义的印象就是负面的。您觉得文化守成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在概念上有什么差异?
杨:与文化保守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是政治自由主义,这个解释框架在政治层面的含义比较多,比较适合20世纪以来思想史的解释传统。如果我拿文化保守主义去研究孟子,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也有政治自由主义。有的概念适合于特定的时间,比如我们讲宋明理学,可以大谈特谈理欲之辨;讲孟子,谈理欲之辨太多了,好像就有点离题了。保守和守成在概念上的区分,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感觉很明显:“保守”有点贬义的意思,而“守成”多多少少有点褒义,至少中性的含义比较强。
文以载道之“道”
宋:刚才我们提到文以载道,这是孟子的一种实现方式,实际上也可能是您的一种观念。那您心目中的道是什么?或者说理想是什么?
杨:刚才讲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,解释了他的仁且智(以性善论为核心)、经权之辨,还有知识分子的士仕观。如果联系道德理想主义,这个道就包括这三个方面。
第一点,人性本身还是善的。我接受孟子的观点。但是,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,却出现了很多让我们难以想像的事情。前不久,南京有个88岁的老爷爷摔倒了,没有人敢去救,他就这么死了。这件事跟以前的一个判例密切相关,就是彭宇案。扶老,按照孟子的观点,就是为长者折枝。为长者折枝,难道是你不能的吗?你不过是不为而已。为什么我们明明能够做的事,却不去做了?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以这样一种假定,即首先以一种恶的心理来推测扶老太太的人?彭宇把老太太扶起来,为什么反而赔了钱?就是因为法官判案,用的人性基本原理是性恶论:既然不是你把老太太碰到的,你为什么去救她?所以我坚信:性善论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命令,一种绝对命令。小孩即将掉下井的瞬间,你的手为什么同时伸过去了?就因为内心里有个东西在命令我们,这个命令就是人性本善。我认为社会必须要相信的一个“道”,就是人性本善。
第二点,经权之辨也很重要。孟子谈到过两种权变:一种是比较激进的,比如说男女授受不亲,嫂子掉到河里了,为什么要去救嫂子;另一种是比较温和的,比如说是否遵守规范。关于经权之辨,我的基本理念是:嫂子掉水、汤武革命之类很简单,这种事情不会经常发生,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要弘扬的东西;应该弘扬的是——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要遵守规范。我们这个时代,遵守规范的温和权变智慧,比救不救嫂子、汤武革命对不对,更加根本。我认为,这个“道”就是要按照规则办事。它看起来很简单,但做起来实际上太难、太难了。
第三点,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。“学而优则仕,仕而优则学”,知识分子是不是一定要去当官,才叫为政呢?孔子认为:你在家孝敬父母,也是为政。同样,我们在家孝顺父母,在单位做好本职工作,这也是为政,也是参与社会很重要的方式,也是在影响政治。
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。我们相信人性本身都是善的,相信要遵守规范,相信在家孝敬父母,在单位做好本职工作,也是在参与政治,这些看起来平平淡淡,但却是真正的道的体现。客观地说,我们生活的世界,物质的诱惑太多,网络和所谓的被提醒、被暗示很多。我们一旦把它们屏蔽掉、去掉之后,剩下的道就这么简单。假设我们这个社会90%以上的人能够做到上面三点,这个社会就“太平”了,所谓的幸福指数绝对可以提高。
宋:对于行善,如果每个人都做到,肯定是非常完好的。但是,包括像西方的制度设计,站在性恶的角度考虑,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。张灏批评中国缺乏忧患意识,过于受性善的影响,忽视如何去制止或者制约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事情。这种批评对不对?性善是不是仅仅是一种理想的东西,很难再行得通呢?孟子提出来以后,两千多年来,我们社会中这么多的恶,如何做到让90%以上的人做到您说的三点?
杨:再回到道的概念,道与器要配置在一块,道德的理念和制度的设置要配合在一块。就现代社会的治理而言,光有道是不行的,还得有器。性善论是一个道,相应地,还要有制度设置来保护这种善,对那种恶进行惩罚,这是基本思路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制度设置跟道德理念归结为依法治国、以德治国,又落实到彭宇那个案例里,就要求法官必须内心里相信:当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上,有人肯定会不由自主地、情不自禁地去帮忙,把他(她)扶起来。如果法官都不相信性本善这个理念,那社会还有什么救呢?所以,制度设计要相应地建立起来。恶在任何时代都有。孟子也不是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善的。性本善的第一层面设定性本善,通过救小孩这些简单的例子来说明;第二层面设定性必须向善,有向善的可能。孟子没有说过没有恶。
“孔孟并称”与“道统”论
宋:前两年有家报纸给我出了个题目:“孔孟之道”合称是否是历史的误会,把孔子思想引入了歧路?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?您对孔孟之间、孟荀之间的异同如何看待?
杨:应当进行文献学上的仔细考证。孟荀并称,就是《史记》里的《孟子荀卿列传》,叫“孟荀齐号”。王充的《论衡》有两篇文章,一篇《问孔》,一篇《刺孟》。可能有人会说:这不就是孔孟并称吗?可我们不能说王充就直截了当地有了孔孟并称这样的提法。
按照文献,孔孟并称始于东晋。晋成帝咸康三年(337),袁瓌、冯怀写了一篇《上疏请建国学》,里面讲到:“孔子恂恂,道化洙泗;孟轲皇皇,诲诱无倦。”这是我所见过的文献里面孔孟并称较为明显的一次。最明显的同样出现在东晋。《宋书》卷22《乐志四》录义熙年间(405—418)何承天的《鼓吹铙歌十五篇》,有一篇叫《上邪篇》,里面写道:“承平贵孔孟,政敝侯申商。”葛洪《抱朴子内篇·塞难》也说:“子以天不能使孔、孟有度世之祚,益知所禀之有自然,非天地所剖分也。”不过,《抱朴子内篇》讲的“孔孟”,许多注家如王明均认为是“周孔”之误。
当然,我们看东汉应劭的《风俗通义》,甚至更早期的作品,也谈了孔子、孟子,如孔子厄于陈蔡、孟子困于齐梁,再谈了荀子,孔孟荀都谈了。但是,孔孟并称的真正出现应该是东晋袁瓌、冯怀以及何承天的时候。唐以后,孔孟并称比较多了。特别是到了宋神宗的1084年,孟子被封为亚圣,孔孟并称就很普遍了。
孔孟并称到底恰不恰当?首先它绝对不是历史的误会,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孔孟之间也有差异,比如二程讲,孔子只说一个“仁”字,孟子说“仁义”,加了一个“义”。虽然有差别,但他们在思想的脉络上是一致的,孟子很明显地说过最愿意学习的就是孔子。所以孔孟连在一块,是很有道理的。孔子、孟子对于一些历史人物,比如管仲、晏婴,看法不一样,很正常。如果孟子的看法完全跟孔子一样,那孟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孔子讲性相近,孟子讲性善论,如果孟子也讲性相近,那孟子就不必存在了。他们之所以并称,就是因为他们既在同一个大轨道上,同时又能相得益彰。
宋:从这个问题延伸出来,就是后来说的道统。近代以来,对道统是否定的。郭店楚简出来以后,子思那些东西出来以后,现在又重提这个问题。您怎么看?
杨:《孟子》里,子思出现过很多次,孟子对子思有高度评价,但没有说两人有师承关系。两汉时期,除了司马迁,大多认为孟子以子思为老师。汉魏之际,《孔丛子》讲得很明显,说孟轲跟子思进行对话,有五六条这样的记载。李学勤先生认为,《孔丛子》未必完全是假的。后来,南朝梁武帝萧衍写了《中庸讲疏》。把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里抽出来,梁武帝可能是第一人。到了唐代,从唐初到安史之乱,孟子被关注的程度比较小,但韩愈之后,韩愈的学生李翱的《复性书》明确认为孟子就是子思的学生。思孟一家,宋代就普及了。这是从传世文献的脉络来梳理。
郭店简出来之后,子思跟孟子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广泛,证明思孟之间存在比较深的联系。《孟子》里有些话跟《中庸》里有些话异曲同工,可以相互比看。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,这是个考证问题,但是子思、孟子在思想上的继承关系十分明显,思孟学派肯定是成立的。陶潜写的《圣贤群辅录》,也明确谈到孟氏之儒。
宋:思孟学派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考证问题,但道统却不同。您认为今天重提道统这个说法有没有价值?是否还需要修正,或者有没有新的道统说?
杨:值得提。道统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:第一是十六字心传,第二是尧舜禹、汤文武一脉相承。十六字心传的若干字眼,《论语》里出现过,《荀子》里也有,《荀子》明确提到“道经”。可以说,十六字心传的基本组成部分,《论语》《荀子》已经体现出来了。清华简《保训》记载文王临终前对武王说的话,也涉及到大量的“中”字。再就是人物线。后来的道统论千姿百态,有以帝王为道统,以知识分子为道统,有以心学为道统,以理学为道统,这里就不讨论了。我觉得,道统应当提倡!比如十六字心传,我认为它是真的,现代人的心灵实在应当净化一点,应当专一点,还应当在心灵的经与物质的纬之间建立恰当的关系。

谨慎乐观看儒学未来
王希孟(后面简称王):您对当前的文化生态有何看法?
杨:文化生态、文化心态,可以分开来谈。生态这个东西是有客观性的维度。我们置身于某种文化氛围,可以说就是一个文化生态。这个生态对我们来说是既定的事实,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网络社会、快餐社会、娱乐社会,我们都置身于其中,谁也改变不了。所以最关键的是文化心态上怎么调整。
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有过一场辩论赛,题目是:做伪君子好,还是做真小人好?上课时,学生告诉我:“做伪君子好”的一方,辩胜了。我在《人民政协报》(2011年5月9日)发了篇文章,认为当代社会,伪君子并不是一个好概念,如果只能非此即彼,做真小人更好。那篇文章也贴在我的博客上,北师大搞马哲的张曙光教授留言,认为还是做伪君子好,不能做真小人。回到辩论赛,“做伪君子好”的一方胜了,我感到很奇怪,也感觉到我们整个文化心态已经发生重大转变。所以,坚守孟子讲的这个道那个理,虽然我认为很重要,但这只是我一个解读者的认识,别人可不这么认为,这就两难了。
王:那您认为儒学是否能有一个创造性转化,可以适应于现代社会?也就是说,您对于儒学的未来是抱乐观的态度、谨慎乐观的态度还是悲观的态度?
杨:谨慎乐观吧!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,文化,不管是哪一种文化,都是边疆的,都处于边缘的位置。儒家思想怎么慢慢地从边缘位置上,对中心施加某些作用,是比较值得思考的问题。现在也有新道家、新法家、新墨家被学者提出来了,光是名字上加一个“新”字,未必就是新的。要真正地创新,我觉得难度较大。继承与创新之间,关键还是继承!现在我们经常谈这创新那创新,事实上做到了多少?真正要想创新的话,最基础的还是继承。只有把继承做好了,创新才能左右逢源、源源而来、水到渠成。
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学者,特别是做文史哲方面的学者,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立足于创新,而是要立足于继承。有些书目一定要读一读,尤其是经史子集里常见的经典,那里面的智慧绝对是无穷无尽的。不要一想着阅读,就是为了创新,一定不要抱这种功利目的。你抱功利的目的写文章,写出来的急就章没有太大价值。相反,安静地、平心静气地看一个作品,才会真正感觉到里面有个很大的世界,而且看的时间越长,那些思想、素材跟你以前内心里的某种期待就会结合在一块,这个时候才可能有比较有意思的论文产生。千万不要为了创新而去写文章!先要把资料做好,阅读量要大,阅读面要广,做好了,自然而然,你对问题的了解就会越来越深,也才能真正地成一家之言。
(杨海文,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,原载《孔子文化季刊》总第9期。)
- 上一篇:没有了
- 下一篇:杨海文:孟子与“初唐四杰”